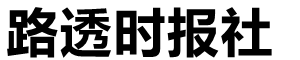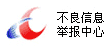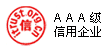本篇文章2912字,读完约7分钟
英格兰,布莱克浦――“永远的雷蒙斯(Ramones)!”本月早些时候,C·J·雷蒙(C. J. Ramone)在布莱克浦举办的“叛逆音乐节”(Rebellion Festival)上,冲着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叫道;咆哮在鲜艳的粉红色莫西干头与漂成金黄色的刺猬头的人海中蔓延开来——其中还点缀着不少正在谢顶的脑袋。
40年前的夏天,雷蒙斯乐队坐飞机来到伦敦,于7月4日在卡姆登的圆屋(Roundhouse)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很多人认为这场演出标志着朋克摇滚在英国的起飞时刻。

乔伊·雷蒙(Joey Ramone)左,与迪迪·雷蒙(Dee Dee Ramone)在1976年7月4日的伦敦圆屋演唱会上。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一支罕为人知、名叫“性手枪”(Sex Pistols)的伦敦乐队在曼彻斯特的小自由贸易厅做了一场演出。据说当时只有几十个人出席,但是这些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乐队。
“我以前说过这话,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嗡嗡鸡”(Buzzcocks)的史蒂夫·蒂格尔(Steve Diggle)前不久在伦敦接受采访时喝着健力士黑啤酒说道,“如果耶稣是在伯利恒诞生的,那么英国朋克就是在曼彻斯特的那场演出上诞生的。”
为了庆祝那个夏天的周年纪念,“朋克伦敦”(Punk London)活动目前正在伦敦全市举行,它将持续一年时间,由一系列展览、座谈和演出组成,该活动由市长办公室和国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提供支持。这个由公共机构赞助支持的反体制活动引来了怀疑和一点嘲笑,甚至是一些温和的抵制行动,这或许证明了朋克的反叛精神还没有隐没在摇滚历史书里。
“我们在BBC新闻(BBC News)听到了我们的歌,”61岁的尼尔·马丁(Noel Martin)在布莱克浦的音乐节场地外面说,他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立的“威胁”(Menace)乐队,他们的歌也成了这次庆祝活动的一部分。那首歌《G.L.C.》是“大伦敦市政会”的缩写,靶子直指市政府,其保守派曾经主张禁止朋克演唱会。“40年前,BBC曾经禁播过这首歌,怎么现在又放起它来了?”
3 月,时装设计师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和“性手枪”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的儿子乔伊·科尔(Joe Corré)认为这场纪念活动意在笼络人心,发誓烧毁价值500万英镑(约合646万美元)的朋克纪念品以示抗议(这个计划在今年秋天举行的活动,马上就被一位市政府工作人员列入了“朋克伦敦”的官方网站)。

“缝隙”的特莎·波利特(Tessa Pollitt)、阿丽亚娜·福斯特(Ariane Forster)、帕洛玛·罗梅罗(Paloma Romero)与维夫·艾伯丁,1977年。
7月,缝隙(Slits)乐队的维夫·艾伯丁(Viv Albertine)访问大英图书馆,参加一场“朋克伦敦”的座谈。她在图书馆举办的朋克历史展前驻足,用永久记号笔在展览的标志牌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些著名女性朋克艺术家的名字。
“还有女人们呢!”她在一个标牌上写道,还涂掉了上面几个男子朋克乐队的名字,写上了几个由女人主导的乐队,比如“苏克西和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和“ X-Ray Spex”之类的。
1976年夏天的那些演唱会成了催化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朋克开始闯进英国的公众视野。“冲撞”(Clash)、“嗡嗡鸡”和“该死的”(Damned)吸引了全国的目光。“性手枪”成了小报上的热门话题,既是因为他们疯狂的举止,也是因为他们过分的歌词,特别是那首《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这是一首反对君主制的宣言,说女王是“法西斯政权”的头子。
新闻媒体迅速做出了反应:“性手枪”的歌在BBC遭到禁播,包括《上帝保佑女王》和《英国无政府主义》(Anarchy in the U.K.),有报道称乐队成员在希斯罗机场冲工作人员吐口水、大叫大嚷,之后乐队被他们的唱片厂牌EMI开除。
几个月后,“性手枪”以花哨的方式解散,但是“雷蒙斯”挺过了接下来的20年时光(C·J·雷蒙是在80年代末期加入乐队的)。

“嗡嗡鸡”的约翰·马厄(John Maher)、史蒂夫·蒂格尔(Steve Diggle)、皮特·谢利(Pete Shelley)和史蒂夫·加维(Steve Garvey)。
布莱克浦是爱尔兰海(Irish Sea)海边的一处度假胜地,来这里参加“叛逆音乐节”的歌迷和乐手们注意到了体制对朋克的接纳显得多么不和谐,但他们也说,英国朋克场景仍然生机勃勃,甚至还在发展。
“我们每星期都看演出,这儿、曼彻斯特、伯明翰,”音乐节第一天,51岁的朋克乐迷格雷厄姆·诺里斯(Graham Norris)边吃着热狗边说。
“有不少好乐队出现,有很多呢,”诺里斯说道,他拄着一支拐杖,头发末端系着一根假的绿色雷鬼辫。“也许他们的爸爸是朋克,也许他们的妈妈是朋克,于是他们也就玩起了朋克。”
音乐节的阵容反映出这种几代人融合的精神:既有“不可知论前沿”(Agnostic Front)和“嗡嗡鸡”这样的早期乐队,也有“年轻男人”(Youth Man)和“愤怒渴望”(Angry Itch)这样的新乐队。
主会场之外,一群年轻的朋克歌迷聚集在走廊里,抽烟、大口喝酒。18岁的康纳·麦克弗森(Connor MacPherson)来自“抗菌剂”(Antiseptics),他们曾在“朋克周末客”(Punk Weekender)上演出,这个系列演出面向年轻人,于7月份在圆屋举办,那是为了纪念“雷蒙斯”的那场演唱会。麦克弗森说,在英国政府由保守党控制的当下,朋克精神仍然有意义。

在40年前的夏天,“雷蒙斯”来到伦敦,于7月4日在卡姆登的圆屋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麦克弗森自称为“有无政府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他对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抨击获得了热烈的回应。
“我们的政府根本不关心年轻人,也不关心劳工阶级,”他说。“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朋克——我们比1977年的时候更需要朋克。”
62岁的奈拉·贝林佐尼(Nella Bellinzoni)在音乐节的场馆里贩卖包袋和手工编织的毛衣。她的头发染成蓝色,用发胶固定成垂直的形状,大概有一英尺高(她说她用了一罐半的发胶,花了三个小时才弄成这样子)。贝林佐尼说自己是“老朋克,从一开始就是”,她看好朋克的未来。
“它变得愈来愈强大,”贝林佐尼说,她是意大利人,现在住在布莱克浦附近。“这些孩子们的爸爸或者妈妈是朋克,然后他们也就成了朋克。”
这样的亲子二人组中就包括了50岁的西蒙·雷诺兹(Simon Reynolds),他带着15岁的儿子奥斯卡(Oscar)坐火车从伦敦来到布莱克浦。
雷诺兹是从80年代初开始听朋克的,他说他认为朋克运动自从早年阶段以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自己的行为,发展为一种“良知”。
奥斯卡留着绿色的刺猬头,穿着朋克乐队“Gnarwolves”的T恤,他说自己大约是在八年前,通过玩滑板和父亲的渠道开始对朋克感兴趣的。他说自己欣赏朋克对劳工阶级的同情,而且喜欢这种和朋友们都在听的东西截然不同的音乐。
被问到和自己的父亲置身同一个音乐场景里,会不会觉得奇怪,他看上去稍微有点狐疑。“不,不,”他咯咯笑着说,然后板起脸来说道,“我爸爸很棒的。”